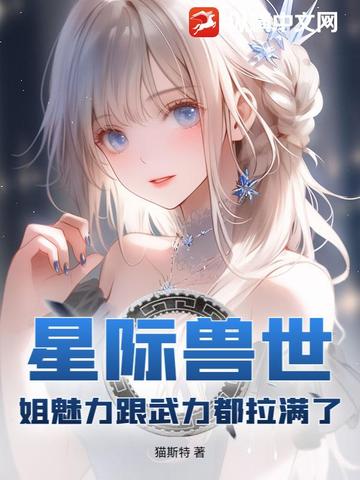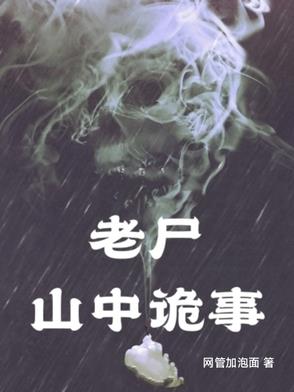第90章 真正属于“我自己”的语言情绪(2/3)
简短词语、甚至动物叫声组合出一个故事的轮廓。
我听了五分钟,一句话都没听懂,却依然笑出了声。
什穆坐在我身边,点了根旧式的燃烟草,他深吸一口气后说:“你们构建了那么伟大的语言,却忘了,人说话,不全是为了让人听懂。”
我望着他,没说话。
“很多时候,我们只是想找个理由,打开自己的嘴巴。哪怕说出来的没人明白,也比不说强。”
我点点头,低声说:“你说的对。”
他转过头来看我,语气认真,“你在塔中心太久了,忘了语言的‘荒草期’。它原本就是野的,不是现在这样被一条条语义协议驯服得像教科书一样。”
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写塔语时的模样:那个在母亲葬礼后,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,手指发抖,眼眶发红,却执意一笔笔在纸上写下“我好想你”的年轻人。
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,也没想过谁能看懂,只是想把那份难以言说的情绪推给世界,哪怕世界听不见。
我忽然意识到——我曾经就是这个村子的一部分。
是塔语把我带离了它。
是我一次次地教别人“怎么写”,却渐渐忘了自己最初“为什么写”。
我带着纸和笔去了村子里那所尚未完全废弃的语言所,它曾是塔语推广基地,如今只剩空椅、断屏和一间未被拆除的“沉默室”。
沉默室原本是用来为情绪不稳定的个体提供语言安抚的地方,但这里的“语言安抚”并不指系统语频调节,而是指“陪伴”。
我坐进那间屋子,四周贴满了字条,有的清晰、有的模糊,有的甚至只剩半个字母。它们大多数都不是完整语句,但却能组成一种奇妙的气氛,就像是你走进了别人的回忆片段中,每句话都在等着你去对它回应。
我拿出笔,在墙上一块尚空白的角落写下了:
“语言不是通道,而是入口。你以为你在把自己送出去,其实你是在打开自己。”
这句话写完,我忽然感到轻松得不可思议。
我没有被翻译、没有被记录、没有上传,没有人提示我“这句话共鸣率不足”或“逻辑不清晰”,更没有人将这句话纳入归档提取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