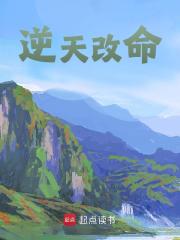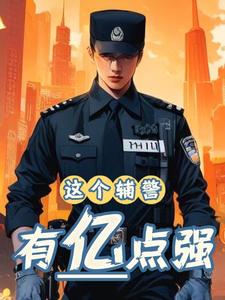第303章 埃及之行(二)(5/8)
许仙读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时,感觉就和读《湘西》一样,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相似的满足与悦乐。
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,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,再来搜集资料,论证成书的。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,进行先是个别的、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。
完整的、严密的体系的形成还是将来的事。但在沈从文这本书里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,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,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。
沈从文这样评价自己的着作: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,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。给人印象,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,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、分章叙事的散文。”(《服饰研究》引言)
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应是理解乃师的,“沈从文后来‘改行’搞文物研究,乐此不疲,每日孜孜,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,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。他搞的那些东西,陶瓷、漆器、丝绸、服饰,都是‘物’,但是他看到的是人,人的聪明,人的创造,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。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,赞叹不已。样子真是非常天真。他搞的文物工作,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,叫做‘抒情考古学’。”
沈从文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,这在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。
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,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,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。
沈从文对人特别是对普通百姓一往情深。
他看到银琐银鱼,会想到小银匠一边因事流泪,一面用小铜模敲击花纹;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,能发现手艺人的情结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。
沈从文用心于工艺美术,用心于物质文化史,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“有情”,和一般的关注文人字画什么的有很大距离。
根本上看,这个文物研究的着眼点,其实也是沈从文的文学的着眼点。
读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也能感受到沈从文的“有情”,在《敦煌壁画唐代船夫摹本》一节中,沈从文极自然便谈到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