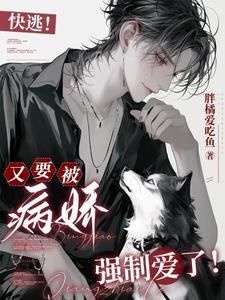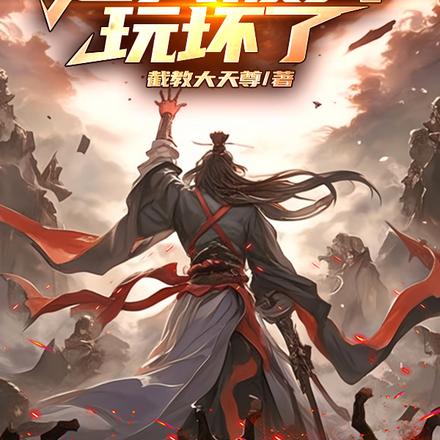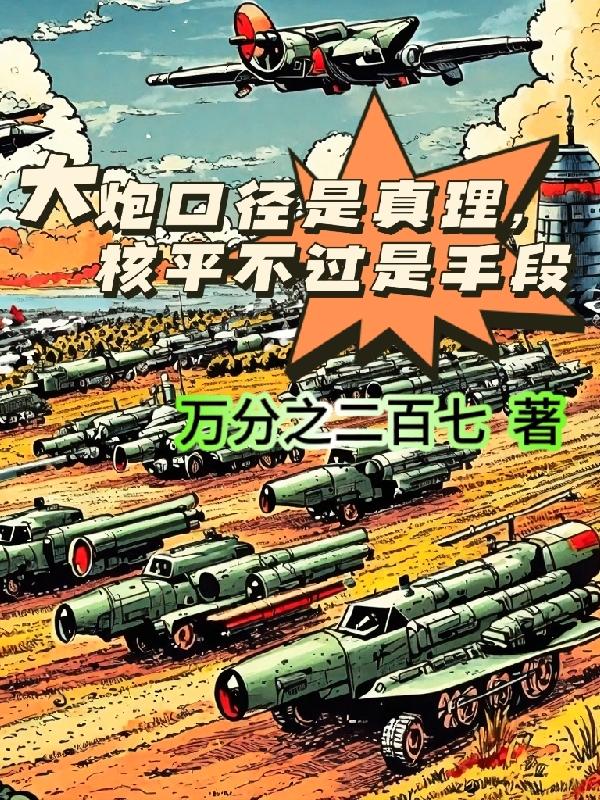第二章:先秦(4/17)
不讲。这是他们的“非攻”主义。他们说天下大害,在于人的互争;天下人都该视人如己,互相帮助,不但利他,而且利己。这是“兼爱”主义。墨家更注重功利,凡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情,才认为有价值。国家人民,利在富庶;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,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。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,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。他们主张“节葬”“短丧”“节用”“非乐”,都和儒家相反。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。他们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,能够赏善罚恶;这也是下层社会的旧信仰。儒家和墨家其实都是守旧的,不过,一个守原来上层社会的旧,一个守原来下层社会的旧罢了。
压根儿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。道家出于隐士。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“避世”之士;他们着实讥评孔子。这些人都是有知识学问的。他们看见时世太乱,难以挽救,便消极起来,对于世事,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。他们讥评孔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,费力不讨好;他们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、独善其身的聪明人。后来有个杨朱,也是这一流人,他却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了,建立“为我”的学说。他主张“全生保真,不以物累形”;将天下给他,换他小腿上一根汗毛,他是不干的。天下虽大,是外物;一根毛虽小,却是自己的一部分。所谓“真”,便是自然。杨朱所说的只是教人因生命的自然,不加伤害;“避世”便是“全生保真”的路。不过世事变化无穷,避世未必就能避害,杨朱的教义到这里却穷了。老子、庄子的学说似乎便是从这里出发,加以扩充的。杨朱实在是道家的先锋。
老子相传姓李名耳,楚国隐士。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,受周文化的影响很少;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。孔子遇到那些隐士,也都在楚国,这似乎不是偶然的。庄子名周,宋国人,他的思想却接近楚人。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,都遵循一定的公律,在天然界如此,在人事界也如此。这叫作“常”。顺应这些公律,便不须避害,自然能避害。所以说,“知常曰明”。事物变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极则反。处世接物,最好先从反面下手。“将欲翕之,必固张之;将欲弱之,必固强之;将欲废之,必固兴之;将欲夺之,必固与之。”“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,大辩若讷。”这样以退为进,便不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