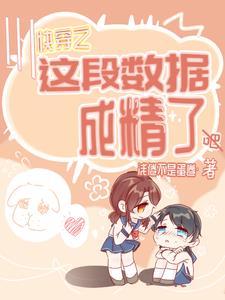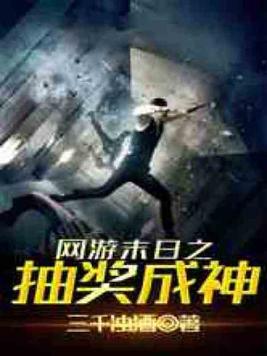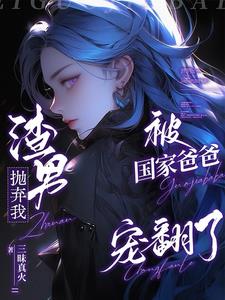第四章:隋唐五代(39/57)
袭古题,唱和重复,于文或有短长,于义咸为赘賸,尚不如寓意古题。刺美见事,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。曹、刘、沈、鲍之徒,时得如此,亦复稀少。近代唯诗人杜甫《悲陈陶》《哀江头》《兵车》《丽人》等,凡所歌行,率皆即事名篇,无复倚傍。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、李公垂辈谓是为当,遂不复拟赋古题。
昨南(各本无“南”字,依张校)梁州,见进士刘猛、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,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。余因选而和之。其有虽用古题,全无古义者,若《出门行》不言离别,《将进酒》特书列女之类,是也。其或颇同古义,全创新词者,则《田家》止述军输,《捉捕》词先蝼蚁之类,是也。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,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音(似当作“旨”)焉。
他的见解以为汉以下的诗有两种大区别:一是原有乐曲,而后来依曲调而度词;一是原来是诗,后人采取其词,制为歌曲。但他指出,诗的起源虽然关系乐曲,然而诗却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。历史上显然有这样的趋势。最初或采集民间现行歌曲,或乐人制调而文人造词,或文人作诗,而乐工制调。稍后乃有文人仿作乐府,仿作之法也有两种:严格地依旧调,作新词,如曹操、曹丕作《短歌行》,字数相同,显然是同一乐调,这是一种仿作之法。又有些人同作一题,如罗敷故事,或秋胡故事,或秦女休故事,题同而句子的长短,篇章的长短皆不相同,可见这一类的乐府并不依据旧调,只是借题练习作诗,或借题寄寓作者的感想见解而已。这样拟作乐府,已是离开音乐很远了。到杜甫的《兵车行》《丽人行》诸篇,讽咏当时之事,“即事名篇,无复倚傍”,便开“新乐府”的门径,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了。
当时的新诗人之中,孟郊、张籍、刘猛、李余与元稹都还作旧式的古乐府,但都“有新意”,有时竟“虽用古题,全无古义”。(刘猛、李余的诗都不传了。)这已近于作新乐府了。元稹与白居易、李绅(公垂)三个人作了不少的新乐府(李绅的新乐府今不传了),此外如元氏的《连昌宫词》诸篇,如白氏的《秦中吟》诸篇,都可说是新乐府,都是“即事名篇,无复倚傍”的新乐府。故我们可以说,他们认定新乐府为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最适宜的体裁。
本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>>>